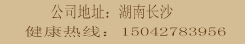杨婷丹,陕西宝鸡人,毕业于宝鸡中学,现为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级本科生。
“黄埃散漫风萧索”,这句其实只描述了陕西的局部气候,“地贫屋陋人憨憨”也是实打实的误会。就拿宝鸡来说,它地处八百里秦川之上,也就是地理概念上的渭河平原,土地平坦,日照条件优渥,水源也相对充足。这般环境,既可以生长出滋味浓郁的眉县猕猴桃,果肉绵密,咬一口整个口腔都充斥着酸酸甜甜的果汁儿,也可以哺育出勤劳坚毅的黄土儿女,一代又一代陕西人通过厚实的生命体验,走向达观的人生境界。
黄:黄土沉默
宝鸡虽然不至于有千沟万壑,但在前些年,其下辖的农村却不乏险峻的黄土峭壁。幼年跟着爷爷奶奶在乡下住的假期总是令人期待,这是包括我在内的一群小朋友的冒险之旅。
夏日中午日头正盛,唯有院子里的核桃树下有方寸的阴凉,塑料袋、烂布条和空药瓶在不远处有气无力地堆在一起,似乎被令人眩晕的烈日晒得蔫蔫皱皱,大有化作一滩热水再也不分彼此的架势。
(故乡的西红柿)
大人们都在午睡,我却永远不知疲倦,倚在树下百无聊赖地摘下一堆树叶揉碎、捣烂。那个季节的核桃尚未成熟,青皮包裹着坚硬的内核,小小一个,只能观赏不能入口,我有一回实在忍不住偷偷摘下一个,想把那层青皮用牙齿捣碎,最后得到的结果自然只有满嘴的涩味。
耳边撕心裂肺的蝉鸣虫叫之声吵得人不胜其烦,不知道在树下等了多久,终于看到“探险小分队”在院门口冲我招手,我跳起来跟上他们,一起往麦场的方向跑去。
渐渐地,道路两边的绿意消退,入眼尽是土色,一座近乎直立的黄土山体和一条一米来宽的上山之路在此处沉默。然而,黄土绝不是枯萎的意象,陕西的土地不是扬尘、不是散沙、而是自然凝结成的块垒,坚固、粘性十足。我们放弃通向麦场的大道,顺着那条危险刺激的小路一点一点往山上挪移,一边是绝壁,一边是悬崖,就像盘山公路,没有任何旁路,也不存在保护设施。一路上,心脏锤击胸膛,到了特别窄的地方,大家就一起趴在地上,试探着往前爬,即便山体不是太高,也足以让人心神震颤。
(陕西黄土地)
经过一番“生死考验”,小分队终于抵达山顶,冒险活动顺利完成。看着山下莽莽红尘,只觉自己神勇无比,吃苦耐劳又勇往直前,大概就是那片黄土教给我的吧。
无论是上山、爬树还是在麦地里玩耍,跌了撞了磕了碰了都要自己收拾妥当,大人总是忙碌,只要不严重,他们没有精力操心这种细枝末节的事情。我自小就深知: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的错误自己负责,哭哭啼啼不是黄土人民应有的姿态。难怪秦腔不似黄梅戏般委婉清新,唱到动情处便要吼起来,这样的土地,合该是自在而痛快的。
“血沃之地,必将长出真正的金麦穗和赶车谣。”
黑:封建迷信
十多年前的关中农村时常秘密流行许多封建迷信仪式,比方说哪家盖房动土,总要先去村里最有威望,也就是人们觉得最灵验的“相师”家里求问动土的时辰、开挖的方位和房顶两侧作为装饰的两只鸽子面朝的方向等;若逢家里有人过世下葬,也要找人看块风水好的墓地;还有些上了年纪、长于占卜的女性被称作“神腊婆”,寻常夫妻吵架过了火,妻子兴许会去神腊婆那里问因果,看她和丈夫是不是今生有缘,可以走到最后。
总之,除了庙宇里的神灵,那时的人们还真诚地相信人界和神界、阴界之间存在使者,使者们各有法术。
其中,过阴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神秘活动,在近些年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随着基本科学知识的普及几乎绝迹,但在我还小的时候,曾在村里一户亲戚家中目睹过一次,至今想起仍觉得有丝丝缕缕的黑色雾气漫过。
那天,直到入夜之前,我都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白日里,许多不认识的人齐聚在亲戚家不大的院子里,紧绷着脸忙里忙外,而我年纪小,虽怀满心的好奇,却只能跟在他们身后进进出出,观察大人们都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这块地砖敲碎呢?”我一边蹲在地上问旁边从未见过的叔叔,一边悄悄伸手去探查缺了的那一块究竟有什么玄机,却被急忙走来的母亲拉了起来,“进屋去,不要乱动东西。”
我非常不解,“大家都在做什么呀?为什么屋子里要摆放没有人吃的水果呢?为什么要在地上划来划去呢?我们今天有什么活动吗?”一连串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得到回答,母亲不说话,带我进了里屋,示意我老老实实坐在土炕上,“不论今天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乱问乱动,你要是困了可以睡一会儿。”“那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呢?”“咱们只是来做一个见证,”母亲顿了顿,“要不是赶巧,我就不会带你过来。”
农村的土炕不像电热毯那样可以自在地调节温度,炕的中间和周围一圈的温度并不均匀,有时候烧得过了,就像现在,兴许是加多了柴火、麦秆或者一些废弃塑料,这片炕头烫得人心里发慌。我往边上凉些的地方挪了挪,察觉到事态的不同寻常,乖乖点头。
入夜了,今天来的很多亲戚都挤在炕上,横七竖八地睡倒一大片。架不住困意,我起先也睡着了。然而,人挨着人的境况实在让人很不好受,空气里什么味道都有,最后混合着滚烫的土炕味儿凝结成极度的闷热和焦躁,连喘气都困难,热气蒸腾,从四面八方旋转而来,严丝合缝地包裹着我,我醒了。
这个时候,我在恍惚之中惊奇地发现之前熟睡的伯伯婶婶全都醒着,他们坐直身子,神色肃穆,透过木雕的窗户镂空盯着外间的厅堂。我也转头望去,那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了陈设,一共有四个人,除了这家的主人——一位奶奶和她的儿子,还有两个不认识的男人,一个躺在厅堂的木板床上,一个站在男人身边。
厅里几乎是黑的,只剩烛影跳动,将熄未熄,明明灭灭,使得红与黑绘成了那晚影影绰绰间的主色调。
隔得太远,既包括炕上的我离厅堂里的四人太远,也包括现在的我也离那个时候的我太远,细节早已模糊,只记得躺在木板床上的男人在某个瞬间突然以奇特的姿势坐了起来,然后开始叽里咕噜地说些什么。
旁边的奶奶尝试着问一些听起来仅有他们自家人才知道的家长里短,陌生男人逐一作答。之后,那位奶奶好像絮絮叨叨说了好些家中的琐碎,她的儿子时不时补充一些。奶奶上了年纪,一件事翻来覆去地说,像是要把平日里无法对人言的哀乐全部倾诉——我终于明白,原来这是一场招魂附体的法事,只为求得一个在无数夜里令他们辗转反侧的团圆。
据我所知,如今的农村早已不再进行这些悬异甚至违法的仪式,然而对亲人的思念是一声亘古不灭的回响。逝者长已矣,生者当如何?那位爷爷早逝,头发花白的奶奶独自生活了很多年,她怀着朴素的信念,想用这种方法唤回她的老伴,哪怕只有一天,哪怕招回灵魂是一场旁人看来明知是假的仪式,可她和儿子一点一点攒钱做法、一家一家地请亲友见证,只求能再见一面,再说几句话,给长久岁月里不为人知的痛彻心扉一点点慰藉。在现代科技和高等教育面前,我的这些亲戚何其“愚昧”,可“愚昧”的背后,难道不是人类共有的绵长想念吗?
家乡,家乡!这个词语太过宏大,细究起来包含无数的层面和无尽的意象,哪一个层面都不能完全代表它。而且人在家时,并不觉得家乡有多么好,就像我在宝鸡总是习惯和同学讲普通话,在济南却总想找人说说陕西话。可是,有时候最不明确的词反而影响最大,就像我们提起家乡,心头一动,眼眶一热,这大概就是家乡的意义吧。
(延安宝塔山)
红:社火腰鼓
宝鸡也称西府,西府社火在全国的社火里都是有名的,但社火表演一般不在高楼林立的市区出现,只在宝鸡下辖的一些县城街头热热闹闹地上演。
所谓社火,就是要把表演者用戏曲中常见的妆面和服饰加以装扮,代表某位正直善良的真实历史人物或神话传说人物,并让他们站在用彩带、花篮和绸布等精心装饰的卡车上游街展览。一个完整的社火团,彩车后面常常还需要再配备敲锣打鼓的汉子,一大群打扮夸张且挥舞着花扇子的秧歌队以及威武神气的舞龙舞狮队。除此之外,有些社火团还会有“猪八戒”“秦琼”等人物形象的角色扮演,在街头和人们互动。
说是展览,真是一点也不夸张,每年元宵节前后的这一两天,核心表演者不仅要在彩车上尽力维持所扮人物的表情动作,还要任由大家观赏、拍照。从上午六七点开始化妆换衣,到下午五六点结束,每一个社火团几乎都要演遍县城里的所有主要干道,遇到重点单位或大型景区,还要进到院子里去短暂停留,以供近距离观看,其间的辛苦自然可想而知。若是哪家的社火团选择的表演难度是“踩高跷”,八九岁的小孩子就要在彩车上支起的细细尖尖、一米来高的高跷上穿着戏服站一天,让人在鼓掌惊叹之余又觉着心疼。
(西府社火)
虽然社火听起来是下里巴人娱乐大众的表演,但它其实并不是“农村人”的独门绝技,只是有些村子里的高难度特色社火比较有名。以血社火为例,它为了达到震慑恶徒的表演目的,总要用上假的斧头、剪刀或锥子等道具,尤为逼真血腥,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除了这些特例,其余的社火都是欢快而喜庆的,寄托着西府人民对新一年的无限期待和对正义的不懈追求。
就连“阳春白雪”的各机关单位,诸如县里的教育体育局、卫生局等,每年也不得不邀请一些民间表演者对他们的职工进行排练指导,每个单位都要参与最终的评选,而奖品据说往往是数量可观的香脆麻花。
有趣的是,西府社火总能让我想到安塞腰鼓,同样的陕西精神,竟也孕育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暑假去延安,在枣园革命旧址旁边,一位老伯将畅快的笑意铺陈在黑黄的面容上,白羊肚头巾高高扎起,把火一般的腰带往天空一抛,安塞腰鼓便“咚咕隆咚”敲起来,我立即称叹:“好一个洒脱自在的陕北人!”老伯一行人在戏台上跳跃、舞动,不一会儿又开始放声高歌,在“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乐声里扭起大秧歌。他们大笑着教我们打腰鼓,有力的喊声冲向云霄,“跳起来啊同学们!再跳高点,往前看,不要低头!”旺盛的生命力从每一个动作中散发出来,一如宝鸡社火。
(安塞腰鼓)
也许这就是陕西人的精气神——永远洒脱自在,永远向前看,永远不低头。我想起余华先生的《活着》一书,主人公福贵在旁人眼中也许是所谓的底层人、幸存者,然而他不过是在一心一意地过日子罢了。魏晋时期刘伶醉酒,告诉仆从:“死便埋我”,这固然洒脱,可我认为这种洒脱并不出于“悟透生死”,而是一种虚无。陕西人的潇洒不是建立在虚无之上,而是拥有结结实实的、能承受生命之重的力量,他们怀抱着由内而外的对生活的无限渴望,才会把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日子也过出惊涛拍岸般的澎湃激昂。
我大约在初二之前的每一个正月十五都要早早去外婆家等候,他们家的房子临街,正好可以趴在窗边看一个接一个的社火团走过。那个时候,小小的窗口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小孩子们你推我挤,谁也不肯少看一眼,最后争抢没个结果,大家就各自找空隙把脑袋凑上前去,好像争夺过程中的社火格外好看。后来长大些,没人抢了,各自随意看看,又随意走开。直到我的课业压力越来越大,就再也没有回去看过元宵节的社火了。
行文至此,我突然感到紧张,急忙打电话问母亲如今的县城街头是否还会有社火巡演,会不会因为扰乱交通或什么原因被取缔,母亲回答说还会有。我不禁长长舒口气,幸好幸好,我今年还有机会回家再看一次。
青:历史文脉
陕西的历史文化不必多讲,诸位也一定耳熟能详,从咸阳到长安,秦砖汉瓦、盛唐风流,皆在于此了。但其实除了当过都城的几座城市,不太为人所知的宝鸡同样底蕴深沉。宝鸡古称“陈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典故就在此处。它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也是青铜器之乡,拥有中国唯一一座青铜器博物院。上万件青铜器从这里出土,青铜铭文的吉金华章从宝鸡走向全国、面向世界。
任何钟情古典文学的人在这样的城市里出生,都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走进博物院,屡屡震惊于青铜器浑厚凝重的品格和繁复高妙的铸造工艺——原来我们的祖辈是在这样探索世界。“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陆游在千年前咏叹的秦岭北麓大散关,如今依旧在尽忠职守地护佑这一方土地。“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诸葛亮的传奇一生,终是在岐山五丈原落下帷幕……
(宝鸡雷电之夜)
当我漫步在宝鸡的土地上时,更喜欢去公园路走走。在那里,你能看到街道两侧仿古的路灯、地砖上的历史知识以及远处绵亘不绝的巍巍秦岭。一想到我走过的土地里埋藏着三千年以来中国智慧和审美的结晶,一想到我经过的关隘是曾经一度失去,最终用无数将士的生命换回的故土,一想到令我凝望叹息的遗址里,也留有温庭筠路过时深沉慨叹的诗句,我就感到一种古今相通的感动,觉得自己在那一瞬间可以“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
我庆幸自己生长在历史文化气息厚重的城市里,因为中国的文脉从来都不是掌握在谁一个人的手里,而是遍布中华大地。我感恩这片土地,因为“我还能在众多浩劫后读到前人的筋骨血肉,我还能在大喜大悲后脱口背出一句他们曾经用来形容自己的爱恨离愁。这片土地留给我们后人最大的礼物应该就是这么两件了吧,一件是历史,一件是文化,前者可鉴世,后者可润心。”
进入大学便很少回家了,每当我回去,总是觉得秦岭不再像我上次见它时那样高大险阻,是群山老去还是我已经长大?是否所有幼时觉得不可攀越之山终会相继倾覆,只要一个人变得足够强大?
远山沉默,不知道是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原因还是结果。
不得不说,以上种种,都只是我记忆中多年前的宝鸡。我知道,这些年的宝鸡甚至整个陕西都不再是那个风吹黄土、温厚沉郁的地方,高楼拔地而起,土路改做水泥,收麦不用镰刀,迷信渐渐破除。工业化和商业化给人们带来巨大的便利,所以我从不认为向前发展是多大的坏事。
那些过去在家乡经历过的一切——核桃成熟的狂喜,攀上峭壁的害怕,抓住蝌蚪的得意,摔伤流血的疼痛……它们最终都化作我的一部分,伴随我继续成长。如今的小孩子不能体验其间种种也无需遗憾,因为我也同样不能体验到他们的童年和家乡,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都应该有自己的秘密空间。
秦岭和黄土又一次在我乘车离去时隐没进茫茫雾气。待到红日初升,云开雾散,我在太阳下稳步向前,建国七十年后的陕西也会眺望四方,大踏步朝未来走去。
评语
钱穆先生曾说:“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最先还是其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文化精神。”关中大地亦是如此。作者先以两句锋利的诗表达了多数人对关中大地的刻板印象,再从回忆中的三个侧面将真实的故土缓缓道来:一代又一代陕西人通过厚实的生命体验,走向达观的人生境界。读婷丹的文字,无论是身处沉默的黄土还是倾听豪放的秦腔,只要耐心地寻着她童年的故事,你就能体悟到别致的文化符号与独特的生活体验。就连婷丹对故乡“封建性”的回忆,你都能明显感觉到同五四反叛的和解:千禧一代的作者们不再进行激烈的二元对立批判,而是透过这些记忆碎片诉说一种遥远的、民族的情节:“对逝去亲人的思念是一声亘古不灭的回响。”这并非是我们认知的倒退,而恰恰是这些回忆拼图支撑了我们每个人独特的气质与魅力,这也足以让我们理解婷丹这句深刻而饱含情感的诠释:“陕西人的潇洒不是建立在虚无之上,而是拥有结结实实的、能承受生命之重的力量,他们怀抱着由内而外的对生活的无限渴望,才会把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日子也过出惊涛拍岸般的澎湃激昂。”
——山东大学数学学院级常帆
婷丹的文字如她笔下的黄土地一般,质朴却厚重。提到秦地,提到黄土,脑中总是会浮现出各种故事和传说,如今却觉得它真实而鲜活。大地上覆盖着苍穹,天空下奔跑着孩子,生长于此处的儿女,生来便多了几分自在与坚毅。漫长的岁月更迭里,他们敬畏祖先,敬畏神明,敬畏生活,传承出一方活色生香的文化。神仙鬼魅,社火腰鼓,断碑残垣,所有元素的背后是人们尽致淋漓的悲欢喜乐。山河辽远,沧海桑田,黄土儿女们跳动着的旺盛生命力和对生命的探索,让这里的族人们,生生不息。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级林悦轩
或许是因为同样出身西北,我对婷丹笔下的家乡有着更加强烈的共情,她细腻的描写,有直击人心的力量,让那片黄土地上的人与景都如梦般出现在眼前。每一个到往过陕西的人都能够明白,当我们去诉说那里广袤的山水时,我们的语言只能厚重。这种厚重,根植于百米之深的厚土,根植于千年之久的历史,也根植于陕西人民坚韧厚实的灵魂。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将家乡的各色形貌组织排布,酝酿成独具一格的浓郁乡情。“色彩”或许就是婷丹脑海中牵引乡情的那根丝线。在她的描述中,宝鸡的色彩是鲜明饱满的:“黄”有童年记忆的无垠苍茫,“黑”有人心深处的复杂缠绵,“红”有民俗文化的火热赤诚,“青”有时光流淌的顾盼多情。正是因为这种“用文字串联色彩”的能力,直观印象与情感内核才有了更加深层的维系,才能在读者的脑海中同时勾连起文字想象和色彩感知。这大概就是本篇文章真实感的来源。
这种“真”,不仅仅体现在写实的描写当中,还体现在真诚的情感表达之中。如果要说明陕西人在情感上的坦率,那么婷丹的文字表达无疑能够作为例证。若要用声音说出“我爱你”,那么她的语言是弱势的,但她的每个眼神都在热烈质朴地传达情愫,从这一层面上,她的语言又是强势的。字里行间,尽显一腔深情。结尾时,作者的目光又忽而远眺,望向那八百里秦川,望向沉默的群山黄土,更甚,望向了时代的中国。一个人所受到的文化滋养和他的家国情感,一语足以为人知矣。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级支睿
文章起笔于千年前文人的墨笔诗句与世代口口相传的俗谚,以片面观引出全面,并从黄黑红青四个颜色入手,为读者详尽地展示了陕西的人物风情。作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成长中的所见所闻,为读者掀开八百里秦川的面纱。陕西地处内陆,厚重的黄土覆盖着她,细腻的渭河却也滋养着她。中原沃土,这里的农作物绵甜可口,这里的人民勤劳朴实。乡下的庭院悠闲,蝉声高昂,可小路蜿蜒,这使黄土人民坚毅刚强;烟雾缭绕,人影绰绰,招魂仪式包含着乡下人最朴实的心愿,对思念的共情使愚昧二字无法吐出;社火在县城街头上演,陕西孕育出的文化缤纷多彩,却都指向热烈的盛放;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陕西从不是文化贫瘠的地方,秦岭山兀自伫立着,见证着千年又千年的历史更替。文章收束于记忆,又展望着未来,寄托着对祖国以及家乡繁荣的愿景。同时,字里行间,也窥得作者静默、淡然,又无可奈何的丝缕乡愁。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级张紫叶
说侠女大家可能不信,婷丹在高中同学中一直有这样的称号。她的文风在我的印象中像侠士挥剑尘土飞扬,能一招制敌也能翩翩起舞,文章辞采丰富像出剑前的预备招式,而字字珠玑却像尖刀割喉,同学们读完她的文章后会惊呼、会感叹。这篇文章却让我眼前一亮,原来侠女再潇洒也有想家的时候,这份思念不是梨花带雨的哭诉,而是藏在回忆与憧憬中的深情。
虽然同在关中,西安与宝鸡的习俗与文化内涵还是差别甚大。用“黄、黑、红、青”来形容宝鸡既新颖又更准确不过了。比起说明每个颜色所代表的文化,讲述自己亲历的故事又是更加动人的了。在“黄:黄土沉默”的片段中,作者讲述了小分队探险登山的故事。作者在小时玩耍登上高山深切地感受到北方山之险之高,而黄土又是那样的厚重与不言,黄土那种坚毅而痛快的精神就在作者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种子,这是只有在黄土上长大的人才能得到的启示。在“黑:封建迷信”的段落中,作者极详细地回忆了“作法”的情形,能够看出来这次经历给作者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而这样一个现今极为少见的民间活动也给宝鸡的文化增添了神秘的色彩。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秘密,像湘西就有一种赶尸文化,已经成为当地特色。老母亲的“做法”与她对丈夫的思念让我们动容,这是黄土地孕育出的深情啊,我们渴望团圆,重视人与人之间踏踏实实的感情,迷信的背后我们能看出宝鸡是个多么重情的地方!“永远洒脱自在,永远向前看,永远不低头。”社火的红就像侠女衣襟随风飘扬潇洒的红,作者为我们再现了宝鸡一年一度热闹的场面,而其中乐观积极的潇洒给了作者极大的精神鼓舞。青铜器最能表现宝鸡的历史文化了,作者想要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有着青铜色彩而又不失人文热情的故乡,它的精神与温暖养育了作者,更因为它的文化与发展令作者思念与祝福。
我们可见,在极朴实、生动的回忆与叙述中,作者穿插一些小片段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和对人生的思考,她没有停留于介绍家乡文化和回忆之中,而是很自然地在字里行间表现着理性的为家乡发展的思考和憧憬。结尾处作者有意升华主题将家乡的变化发展与祖国的发展结合在一起,也表达了自己和家乡一起走向光明未来的坚定信念。
虽然西安与宝鸡高铁只要不到一个小时,婷丹的思念也让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家看看,期待着能与黄土里走出的侠女一起回到故里,我们再爬一次秦岭,再捧一抔黄土!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级万欣怡
文章写得很好,作为同龄人的我,感到惭愧。
全文分6个部分,开头结尾和4个小标题。从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深厚的写作功底和对家乡历史的谙熟。文章不仅亲述儿时经历,将家乡的黄土峭壁之险呈现给读者身临其境之感,还夹叙夹议,使自己对家乡的热爱和赞美有了很好的表达。另外动用名言典籍和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使得文章营养更加丰富,可读性更强。所有的写作技巧和作者的呕心锤炼的文字,都使这篇对家乡的回忆与憧憬,能够在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
最难能可贵的是结尾部分:作者谈到“如今的小孩子不能体验其间种种也无需遗憾,因为我也同样不能体验到他们的童年和家乡,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都应该有自己的秘密空间。”“工业化和商业化给人们带来巨大的便利,所以我从不认为向前发展是多大的坏事。”说明作者有一颗积极上进的心,她明白新中国在党的带领下一定会越走越远,越走越好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记忆,但陕西人就是”永远洒脱自在,永远向前看,永远不低头。”相信在未来,家乡可以走向更好的时代,黄土中蕴藏的宇宙能量将是无限大的。
——江西财经大学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级来钰鹏
文字
杨婷丹
图片
杨婷丹网络
编辑
杨婷丹总编辑
周树雨
本文系“山大南路27号”原创
转载请联系授权
白癜风光疗对人体有害吗白癜风好了应该要注意什么转载请注明:http://www.qingpia.com/qpzz/39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