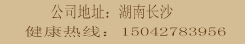![]() 当前位置: 青皮 > 青皮炮制 > 芝士夾心中国饮食也有黑暗一面有些菜式
当前位置: 青皮 > 青皮炮制 > 芝士夾心中国饮食也有黑暗一面有些菜式

![]() 当前位置: 青皮 > 青皮炮制 > 芝士夾心中国饮食也有黑暗一面有些菜式
当前位置: 青皮 > 青皮炮制 > 芝士夾心中国饮食也有黑暗一面有些菜式
1月12日,著名学者王学泰在京逝世,享年76岁。王学泰逝世的消息引起学术圈震动。历史学者张宏杰深感意外,“正如他的力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并不广为人知一样,他一生的学术成就也没有得到我们这个社会充分的认识。”小编特此与读者分享部分内容,向王学泰教授致以深切缅怀。
随着《舌尖上的中国》的热播,越来越多的“吃货”为中国的美食感到自豪,更有网友认为中国的饮食世界第一。然而曾著有《中国人的饮食世界》、《中国饮食文化史》等书的王学泰研究员,在对话凤凰历史时却指出中国饮食中的黑暗面:从古籍中记载的烧活鹅烹活驴,到流传至今的燕窝鱼翅,这些菜式无不展示了人类残忍的一面。这些变着花样来折磨生灵的吃法,源于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把“吃”当做一种娱乐,也反映出中国人缺少精神领域的追求。
此外,王学泰还指出:中国饮食文化中还渗透着等级制度。从解放前百姓称炖肉窝头是“奴欺主”的无心之语,到毛泽东时代干部按级别享受不同的饮食待遇,都清楚地表明:中国饮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子文化,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优缺点。至于社会上对宫廷菜的追捧,也是中国皇权专制制度的后遗症。因为宫廷菜其实既不美味也不健康,并不值得提倡。王学泰认为,中国饮食文化中,其实比较值得传承的还是吃素的传统。
两种伤天害理的食材:鱼翅燕窝
王学泰:很多人说中国的饮食世界第一,我这里引鲁迅先生一段话:“近年尝听到本国人和外国人颂扬中国菜,说是怎样可口,怎样卫生,世界上第一,宇宙间第一。但我实在不知道怎样的是中国菜。我们有几处是嚼葱蒜和杂合面饼,有几处是用醋,辣椒,腌菜下饭;还有许多人是只能舐黑盐,还有许多人是连黑盐也没得舐。”因此,我以为虽然经济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多了,但贫富不均仍很严重,在电视中过度张扬中国食品的精美与高贵,让人怀疑这些与广大民众有何关系?鲁迅的话仍然值得我们思考。
中国人发明了两种暴殄天物、伤天害理的食材,一是鱼翅,一是燕窝。这两种食材在中国饮食上出现很晚,传说源自明初,确切的文字记载是到了明中叶了。大名鼎鼎的《金瓶梅》中言及蔡太师府上下饭的菜肴中就有“燕窝、鱼刺(翅)”与传说中“龙肝凤胆”相并列。到了清代燕窝鱼翅仿佛是最高档宴席的标志了,富贵人家请客不是鱼翅席,就是燕菜席。
所谓“燕菜”就是燕窝,它是金丝燕的窝,多筑于巉岩峭壁之上。金丝燕是比家燕还小的燕子,每年的3月到12月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到南海繁衍后代。它用自己分泌的唾液和从海中衔来的小鱼小虾,在岩壁上筑巢以繁衍后代,筑这个巢需二三十天,金丝燕要在山海之间往来成千上万次,它的坚韧与悲壮不亚于衔微木以填沧海的精卫鸟。我不知道这是谁发现的,这个燕子的窝居然能吃。一些人冒着生命危险,把燕窝从绝壁上采下来,再被商人重金买下,用来煮粥煲汤。其实从营养学角度来看,其成分功能单一,是一种低营养食品。人们吃它,更多是为了炫耀。
更悲催的是鱼翅。人们把鲨鱼捕到船上,把两个翅割下来,再将无翅的鲨鱼抛回海洋,沉入深海中,无法游动、无法觅食,痛、饿、血流不止,最后在深海死去。鱼翅不仅营养上没有特别之处,而且其味道也来自好汤(如鸡汤、鸭汤)的慢火细煨。人们吃它似乎仅仅是为了炫耀自己有钱,这个炫耀就使得鲨鱼即将在大海中灭绝。我们抗议日本杀鲸,但日本人还是把整个鲸鱼吃掉的,我们捕鲨仅仅是为了它的翅。
现代的文明人应该懂得地球不只是属于人类的,人类不能仅仅为了满足一些极其无聊的精神需求(比如虚荣)动辄毁灭大自然中一些物种,破坏生态平衡,展示人类残忍的一面。
传统烹饪中的“残忍食品”
我们传统食品中还有一些残忍食品,不仅仅是个吃什么的问题,而且涉及到怎么吃?吃东西本来只是延续种群的需要,不能在吃饭中培植和放大人性的残忍。社会进步就是社会不断矫正人性中遗留的野蛮部分。因为人类从丛林走向文明,就是不断消减在丛林中所建立的“优胜劣汰”的法则,不断建立文明社会的规则。文明社会规则是什么?善待自己,同样也要善待他人。这种意识是怎样产生的?吴思认为善良是自然产生的,“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就生出这种善的生理基础,无需培养,天生存在。人之初性本善,道德无需外借,而这个性本善大体指同情心和正义感。”我觉得思想意识是与生活方式和人的交往方式密切相关的,当人们在一个需要互相援助的才能生存的群体中,以及人们认识到抢掠高于和平交易成本的时候,为他的意识也就产生了。这种为他意识就是“善性”的根本。孟子发现了这个善性,而且倡导培植这个善性,善待万物、包括动物都是有助于培植善性的。荀子看到人作为一个生物种群是有生物性需求的。《荀子·荣辱》中说人“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这是人作为生物种群必备的,如果没有这些,作为生物种群的人就被灭绝了。荀子认为这是人性“恶”的根本,放纵它不加节制即为恶。他认为善的产生是对人性不断教化的结果,因此荀子注重礼义教化。追逐残忍食品,在荀子看来是放纵欲望的结果。不管是孟子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但在控制人性趋恶的一面是共同的。儒家的产生实际上是华夏民族从野蛮走向文明的一个里程碑。
战国时期,齐宣王看到将被宰杀牛的恐惧,内心不忍,用羊替代它。可是老百姓认为齐宣王以小易大是因为其吝啬,舍牛杀羊。孟子认为这种不忍之心是“仁”心之端,他提出“君子远庖厨”,要远离宰杀的现场。这曾被瞿秋白指责为“虚伪”。孟子认为人的不忍之心源于人内在固有的仁慈的道德本能和道德直觉。其实这是人们脱离丛林和宰杀现场走向文明的标志。孟子力主要抓住这个“仁之端”大力培植,扩而大之,成为仁政。
侯耀文的得奖相声里有一个《糖醋活鱼》,这是歌颂烹饪技艺高超的厨师的。他最拿手的一道菜就是“糖醋活鱼”。这道菜上桌后鱼的眼睛还能动,嘴巴还开合。甚至让人搞不清到底谁吃谁,大家一致叫好,连老外也跟着赞美。我觉得这道菜就是上帝说好也不对。鱼烹熟了还让它不死,这与古代的凌迟有什么区别?当时执行凌迟的刽子手割够规定的刀数之前不能让犯人死。
中国的残忍食品太多,而且花样百出,实际上是折磨万物。唐代有个菜叫“明火暗煨烧活鹅”,就是用火烤活鹅,在笼子外头置放很多碟子,里头有各种佐料,鹅一被烤就渴,渴了就得喝碟子里的佐料,它一喝味就进了身体。后来的蒸活甲鱼也是这路数,在蒸笼里面放置饮料碟,把甲鱼活活蒸死。
清代有个河督衙门,河督的职责是治理黄河,如果黄河泛滥,指挥治河,疲于奔命,这差事特苦,一般人不太愿意去做。但是衙门经费很多,如果这年没出事,河督衙门花销奢侈,最奢侈还是饮宴。河督衙门菜,据《清代野史大观》记载:
尝食豚脯(猪里脊),众客莫不叹赏,但觉其精美而已。其法闭数豚于室,手执竹竿追而敕(chi,鞭打)之,豚号叫奔走以至于死,亟割取其背肉一片。萃数豚之背肉,仅供一席之宴。盖豚被抶将死,其全体精华萃于背脊,割而烹之,甘脆无比。又有鹅掌者,其法笼铁于地,而炽炭于下,驱鹅践之,环奔数周而死。其精华萃于两掌,而全鹅可弃也。每一席所需不下数十百鹅。有驼峰者,其法选壮健骆驼缚之于柱,以沸汤灌其背立死。其精华萃于一峰,而全驼可弃,每一席所需不下三四驼。有猴脑者,预选俊猴,被之绣衣,凿圆孔于方桌,以猴首入桌中,而挂之以木,使不得出。然后以刀剃其毛,复剖其皮,猴叫甚哀,垂以热汤灌其顶,以铁椎破其头骨,诸客各以银勺入猴首探脑食之,每客所吸不过一两勺而已。有鱼羹者,取河鲤最大且活者,倒悬于梁,而以釜炽水于其下,并敲碎鱼首,使其血滴入水中。鱼尚未死,为蒸气所逼则摇头摆尾,无一停息。其血从头中滴出,此鱼死而血尽在水中,红丝一缕,连绵不断。然后再易一鱼如法滴血,约十数鱼。庖人乃撩血调羹进之,而全鱼皆无用矣。
他们吃猪时不是杀死,而是打死,就为取那猪脊背上的一片肉,用几十只猪做成一道菜。烧鹅掌也是这样,把鹅赶到烧红的铁板上,就取它的鹅掌做菜。做鱼头羹手法更为残酷,三尺以上的黄河鲤鱼,把鱼头打破,吊在那儿,火开着,血不断淋,用几十条鱼来做一锅羹汤。
还有种残忍食品,听起来就惨不忍睹,就跟古代的凌迟罪似的。《清稗类钞》记载山西太原晋祠“鲈香馆”烹驴远近闻名:
以草驴一头,豢之极肥。先醉以酒,满身拍打。欲割其肉,先钉四桩,将足捆缚,而以木一根横于背,系其头尾,使不得动。初以百滚汤沃其身,将毛刮尽,再以快刀碎割,饮食前后腿或肚、或背脊、或头尾肉,各随客便。当客下著时,其驴尚未死绝也。
其残忍真令人瞠目结舌!利用这种奇特的“烹饪”法引得客人“日以干计”,可以想见每天会有多少围观者。
当时的山西巡抚巴延三,得知此事,交送按察使审理此案,以谋财害命罪将老板处斩。巴延三是个无德无能无才清宗室,礼亲王昭梿《啸亭杂录》记载了他几件事,对巴延三一句好话没有,唯独干了这件好事,让研究饮食文化的记住了他。
烹驴这件事不仅是对动物残忍,其毒害的不仅是食客,也包括许多围观的人。国人似乎特别爱看枪毙人、杀人等“热闹”。鲁迅说国人“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这是专制社会的特产,自先秦以来,惩治犯人,杀人不是找个背静地方杀,而是“戮之市朝”,就是在朝堂的后边人烟稠密市井中开刀问斩。杀鸡来给猴看,是为了吓唬普通老百姓。这就培养了人的残忍性。
什么叫文明?文明就是不断从野蛮走向不野蛮。不野蛮是什么?不仅善待他人,也要善待万物万类,不要动不动就用暴力解决问题,这才是文明。狮子饿了它才吃兔子,那是食物链,但燕窝、鱼翅并不在人类的食物链上,可人也要千方百计搞来吃,而为此不惜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
现今人们追求异味、野味的狂热令人不解。前两年一个深秋我应邀到河南一个大学讲座,完事后,主人说今天下午我们带您欣赏一下黄河落日,晚饭就在黄河边野店吃吧。下午驱车一两个小时,只在黄河岸边站了几分钟就又驱车到所谓“野店”了。店不大,一排草房,与“野店”名实相副。可是令人诧异的是店外门前停着好几辆小轿车。随主人一进门就有几位学校老师起立相迎。我明白了这是主人安排的小型欢送会。为什么假座于这个简陋的地方呢?待坐下我才明白这个野店是专卖野味的,主人的美意是让我尝一尝大城市少有的野味。菜肴中许多是国家明令保护的野生动物。我赶紧起立向主人致歉,声明我吃素,多谢大家,辜负美意。结果主客都很尴尬。碰巧一位女教师也说她也不能吃野味,皮肤过敏。此时店家过来解围,说他们除了动物野味、还有植物野味。我很吃惊,植物也能制成野味?店家说,他们保存的有今年夏初将熟的青小麦,可以做“碾转”,别有风味。我听说过碾转,河北称粘串,也许是音同字异吧。青黄不接时,小麦已经灌浆,尚未饱满成熟,但饥饿的百姓已经饿得不行了,于是便采青小麦上锅蒸熟,碾下青皮麦芒,再用锅炒,用来果腹,听说此物耐饥,吃多了有撑死的。没想到这种救荒食品现在已经成为美食。这个经历使我奇怪,国人为什么那么追求野味呢?国家三令五申、甚至制定成法律,人们还冒着犯法的危险去一尝禁脔呢?
文革时靠行政手段分配饮食毛泽东批“资产阶级法权”也没用
王学泰:中国自古以来都是。食物短缺的时候,谁有钱谁就能买到吃的,即使是特别艰苦的时候,米能贵到珍珠的价格,柴火像桂枝那么贵的时候,有钱人也能吃得起,买得起。这似乎可用“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来概括。谁钱多,谁就“更平等一些”。
但解放后就不是这样的了。困难时期是按照等级来的,我知道副总理级享受什么待遇。因为某同学父亲就是副总理级的,困难时期一个人每天一斤肉。政协专门有个供内部消费的食堂,政协委员去了都能吃饭,包括宣统皇帝,也带着亲属一块去到政协食堂吃饭。另外,17级到13级之间的干部叫糖豆干部,因为这些级别内,每人每个月可以补助二斤糖、两斤黄豆。总之当时干部级别享受不同的的待遇,分得十分细密,好在现在已经部分解禁,在网上都可以查到。这种做法也可以说在权力面前人人平等。权力大的人就“更平等一些”。
困难时期除了一些极高级的干部按照配给才能吃得比较好以外,可以说95%以上的人都处在饥饿状态中。听我老师廖仲安先生说,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负责人齐燕铭先生,主持在京专家在人民大会堂开个会,讨论由游国恩先生、萧涤非先生等主编的在高等院校使用的《中国文学史》,参加的大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专家,廖先生当时四十来岁还是敬陪末座的。那时正是困难时期,时近中午,大家早已枵腹从公了,可是都是有修养的老先生,谁也不肯开口。
此时齐燕铭先生说“时间不早了,是不是该解决一下吃饭问题了?”游国恩先生说了一句“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大家都笑了,因为游先生回答敏捷而切题。大家来到宴会厅,虽然并不丰盛,但鸡鸭鱼肉都有,在那时已经难得一见了。那次宴席的汤菜是鸭汤,但那鸭子真是不敢恭维,如同木板。有人说太老,有人说这是板鸭。游先生说“鸭之板板”(“板板”出自《诗经·板》“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犹不远。”“板”一般解释为“反”)。游先生这句偶然的戏词,文革当中被当作罪状,整得很苦。
“高知”尚且如此,百姓生活更可想见。从年十年大庆之后,困难开始显现。北京的标志是所有的早点铺都不卖北京人常吃的烧饼油条了(那时所有店铺都是国营的),改卖“菜粥”,二两粮票一碗,没有一点油水。老百姓想吃带油水的,没有,有钱也买不到。现在年轻人很难想象。直到年下半年开始实施陈云力主的货币回笼政策,推出一系列高价食品。例如北京5元钱一斤的高级点心高级糖(就是一般奶糖,正常价格是一元左右,但市场没有)。北京小孩歌谣有云“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茅房”。一些高级饭馆推出5元餐,一餐米饭半斤,一肉菜,一素菜,一汤,能吃饱,这种规格的饭菜,在平常不到一元。平价饭馆的菜肴中没有肉蛋,有也很少。要吃有油水的只有吃这高价饭。有一次我东安市场买书饿了,到饭馆一看,只有米饭素菜。我买了一个最贵的菜——烧双笋,一块三毛多。带端上来一看黑糊糊一盘,“双笋”原来是莴笋、竹笋。竹笋仿佛竹板,根本咬不动,只吃了莴笋和二两米饭,那时我19岁,吃这点东西跟没吃一样。
高价饭不是每个饭馆都卖,当时北京只有七八百家饭馆,其中大部分没资格卖高价饭。北京马凯、同春园、丰泽园、同和居、镇江、大三元等大饭庄子才有。那时饭馆是十点半开门,九点就得去,因为有一定数量,大约也就三四十个号,卖完了,请您明天再来。我有个大学同学,他父母在河北省某县城教中学,教师有定量虽比农民好很多,但也没法与北京比。但他有一坛子现大洋,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深埋在地下。困难时期饿得受不了,但县城里有钱也没有用,没有高级饭馆。老俩口也不敢在县城兑换现洋,只得把现洋弄到北京交给上大学的儿子,就是我这位同学。他每天上午都想法逃课,去吃高级饭馆的5元餐,目的是把粮票省下来给父母寄回家去。那时金银只能国家收购,不许私人买卖,“袁大头”(含银量最高的)1元2角6分一块。同学每天中午简单的一餐相当4块大洋。现在“袁大头”元一块,这一餐相当现在的元。
当时城市工人工资平均四五十元,正常时节可以养三四口人,在困难时期,这点钱处处捉襟见肘,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饭馆没他们的份儿,只有过去的大资本家、当时的三名三高人员(名作家、名演员、名教授;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才敢问津。听说当时农民手中有点钱,这主要是在、刮“共产风”“一平二调风”时把一些原属私人的财产收走了,比如房屋、大型农具、家具、木料、砖瓦等等,年夏季以后落实政策,要求农村干部退回给老百姓,实在没法退的,补给点现金。因为大跃进、大炼钢贴中毁了不少,想退也退不了了,给农民补了一批钱。后来放开高级食品和一些紧俏商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这些钱又收回来了。
直到“文化大革命”时,糖一直是紧俏商品,北京好买一些,外地根本买不到。年初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西安的姚连蔚作为代表到北京开会,没想到被选为“副委员长”。选上之后,他还想回西安,结果要常住北京。他向组织说,来开会时朋友还托我带白糖呢?结果给国务院给他调拨一火车皮的糖回去,西安皆大欢喜,但不知姚的朋友是否买到了。那会儿完全是靠行政手段、靠等级制度来分配饮食。毛主席说这是“资产阶级法权”也没有用。其中力主打破“资产阶级法权”的张春桥自己也在享受着资产阶级法权,要么凭什么北京的工人四五口人挤在一间小房里,他一个人就住钓鱼台的一栋楼?
“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也是商品短缺,特别是食品,因此那里有排长龙的地方大多是卖吃的。但总的说来,特别是北京比困难时期强多了,所以人们一来北京就会被朋友托付代买食品。年代,我下放在北京远郊,每月回京,特别是天冷的时候,就有老乡托我代买猪肉,那时只要多排几次队还能买十来斤的。其它一些地区的老百姓的定量商品就比北京少许多。听说东三省城市居民每个月是肉三两(北京是一次最多二斤,而且不登记在购货本上)、油三两(北京每月油票半斤,其中四两花生油、一两香油)、糖三两(北京白糖随便买、不限制,但有时没有),所以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外号叫“陈三两”(文革前有个戏曲电影叫“陈三两爬堂”)。
饮食中的等级意识:炖肉窝头是“奴欺主”
王学泰:中国饮食文化实际上就是具体而微的中国文化。什么叫具体而微,就是中国文化的缩小件,就跟说女儿是妈妈的复制品似的,什么都像她妈。鲁迅先生说你要想知尊夫人的未来请看老丈母娘现在的样子,他说可能有点进步,你老丈母娘裹脚,尊夫人是天足。老丈母娘过去没种过牛痘,可能得过天花,尊夫人脸上却平平整整,这个有可能。但这是极其局部的改变,大体上中国饮食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子文化,中国文化中的优点和缺点在它身上全都有。
那会儿你吃东西如果讲究过头,一超过这界限就是逾制。所以中国的等级制度全渗透到各个方面去,有时候老百姓不自觉就表现出来。解放前,如果有人问:“今天您吃的什么?”答:“吃的炖肉窝头。”“您这是‘奴欺主’啊!”怎么叫“奴欺主”?因为菜比主食要好。在肴馔中也有等级意识,有不少食材是上不了正式筵席的,外地我不太清楚,起码北京是这样。例如百姓常说的“狗肉上不筵席”就是一例。又如现在视为珍品的如螃蟹、烤鸭等都是作为小吃流行的,可以下酒吃着玩,但正式宴席就没有它们的份儿。这种情况在解放后有了很大改变,当然可能也跟食物短缺有关,食物少了也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
宫廷菜不值得提倡:既不美味也不健康
王学泰:因为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实行太久,所以皇上这一套东西受到人的追棒。实际上皇家没有长寿的,中国出了多个皇帝,活过70岁的不超过10个,过80的就只有清乾隆、南宋高宗,另外还有一个武则天,如果武则天也算皇帝的话。
宫廷菜未必是最美味的菜。因为宫廷制度上有很多限制,不可能让食物的特点充分发挥。比如皇帝吃饭时不吃三口菜,就是为了不让底下知道皇帝爱吃什么,吃两口完了马上就换。又如皇帝不能吃寡妇菜,都得拼菜,经过“拼”,菜肴刚刚出锅的感觉就没有了。我在这里指的是清代宫廷,因为清代宫廷的礼制最为完备,留下的记载也最为详密。不必提倡什么宫廷饮食。它未必是烹饪技艺的高峰,也不一定健康。它只是奢侈、用料珍异,这才为一些人追捧。
除了人们习惯于拜倒皇帝脚下之外,也与吹捧者自己的利益有关。讲个南宋的笑话,宋代皇帝有个习惯常常在首都街市上购买日用品,特别是吃食。南宋更是这样。南宋临安(杭州)有个卖“胼胝药”(治疗脚底板的老茧)的商贩,打出个招牌是“御用”(皇帝专用),皇帝养尊处优,脚底板有什么老茧?这肯定是假广告,官员们向宋高宗汇报了。皇帝下旨让小贩进宫,想给他定罪,但一看小贩愚昧可怜,就放了他。小贩有了这次经历后在他的广告又上加了一句“曾经皇帝传唤”。现在不少广告与此类似。
“西化”反对不了:历来优秀的文化总要代替比它次一些的
王学泰:甚现在一些医疗药物也以“宫廷”作招牌,实际上宫廷的太医用药特别谨慎,怕用错了药,因此,御医都是以警惕、谨慎为第一位的,这反而妨碍了医学的发展。因为医学要探索性的东西,有的时候探索是要冒点险的。现代医学中的临床对比实验、医院制度,全都是西方传来的。我们动不动说反对西化,实际上西化你反对不了。文化从来是低处向高处学习,就跟水从高处往低处流一样。文化没什么侵略不侵略,历来是好的要代替次的,方便的代替不方便的。
辛亥革命之前,好多反对满洲民族主义者以为革命胜利了,就要恢复峨冠博带的汉族服饰,章太炎还设计出来了一种“汉服”,挺像日本和服的,并穿着照了照片,结果革命胜利了,知识人还穿清代的大褂,洋气点的穿西服,孙中山先生根据西装和日本的学生制服设计改装的制服,但在解放前也就是学生和政府工作人员穿,大部分国人穿的还是满洲遗留下的长褂或短褂。后来国民政府还把“长袍马褂”作为礼服,解放初,革命占领一切领域,长袍马褂成为旧社会的标志,西装成为帝国主义象征,服装也要像苏联老大哥学习,于是,“列宁装”登场,双排扣、翻领、斜插兜,城市中的革命女性几乎人人一身列宁装。年,苏联向中国倾销花布,又倡导女性穿“布拉吉”(连衣裙的俄语音译),当时虽有点强制推销,但毕竟美化了城市。可惜没几年,年大跃进,中苏交恶,布拉吉遂绝迹。我们从服制的变化,很难说穿西服就是受了西方文化侵略,穿布拉吉就是受到苏联的侵略。再举一个清末的例子,湖广总督张之洞还是一个洋务派,但他毕竟是“进士出身”对于秘书在往来公文用词“不雅驯”,常有一些新名词夹杂其间很有意见,有一次张之洞批示说,“不许用新名词”。他的幕僚怪人辜鸿铭就说,“名词”也是新名词,因为“名词”本身就是从日本来的,中国古代也没有。
素食为主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王学泰:第一,现在既然我们吃饱饭了,就应该追求点精神上的东西。过去缺少精神生活是因为吃不饱,还可以谅解。现在社会财富大大丰富了,90%以上的人都有饱饭吃,所以应该多追求点精神上的东西。当然我们不能指定别人应该追求什么,但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点精神上的东西,别老停在什么“舌尖”上的中国,应该有点精神上的中国,对吧?别把“吃”推到极端。
第二,在饮食中应该多注意点植物性食品。素食真是对人身体好,按照达尔文的学说,人是从类人猿发展来的,最早应该都是素食动物。另外,中国是农业民族,我们基本上是一个素食为主的民族。即使有点荤食,也是作为副食来看待的,所以还是应该多注意点植物性食品,这对身体也有好处。我们总觉得肉食有极高的营养,实际上未必。
王学泰于年6月3日
以上图文,贵在分享,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转载请注明来源,谢谢!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qingpia.com/qppz/1152.html